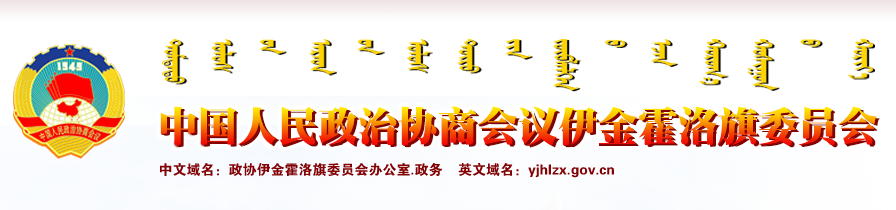郑福田:守护精神家园
导语:郑福田一次次来到草原深处,调研少数民族“非遗”保护,力求真正把问题找准、把原因理清、把建议提实。
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哲学就是怀着乡愁的冲动找寻失落的家园。对于长期沉浸在中国传统文化、“夜半灯青琢旧词”的郑福田来说,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意义也正在于此。2016年,从衰草返青的暮春到瓜果丰硕的金秋,从西部“塞柳当风拂面勤”的阿拉善到东部“托雪松枝更媚柔”的兴安盟,他一次次来到草原深处,调研少数民族“非遗”保护,力求真正把问题找准、把原因理清、把建议提实。近日,围绕少数民族“非遗”保护的话题,他接受了本刊记者专访。
本刊:近年来您一直致力于推动少数民族“非遗”保护,提出了许多颇具社会影响力的意见建议。您为什么对这个问题这么执着?
郑福田:于公于私,这个问题都对我有着强烈的吸引力。
于公,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历史悠久,传统深厚。几千年来,少数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不仅有大量的有形文化遗产,也有斑斓多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神话、歌谣、谚语、音乐、舞蹈、戏曲、曲艺、皮影、剪纸、绘画、雕刻、刺绣、印染等艺术和技艺以及各种礼仪、风俗、民族体育活动等。
这不仅成为各民族赖以绵延发展、增加凝聚力的纽带,也成为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基础以及联系世界的桥梁。保护少数民族“非遗”,就是延续我们的民族血脉、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我很难想象,如果少数民族“非遗”消亡了,我们的精神家园该是多么的荒芜。
于私,我长期在内蒙古工作生活,对于传播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始终十分关注,且愿意为这项伟大的事业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内蒙古少数民族“非遗”丰富而独特,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口头类“非遗”,如说、唱、吟、诵的内蒙古地区的神话、传说、传统故事、童话、歌谣、谚语等;形体类“非遗”,如内蒙古地区的舞蹈、武术、体育杂技、魔术等;造型技艺类“非遗”,如法器制作和勒勒车制作技艺等。
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一直滋润着我的心灵。呼麦那种从嗓音深处发出的声音美轮美奂,简直就是天地之间自然的融合,令我终生难忘。我还曾经写过一首词,描写的就是我小时候看到的乡村婚礼情形:“乳燕梁间软语开,鸣鸾四马驾车来,乡肴村酒摆盈台。端坐新娘眉目秀,侧观联对琴瑟谐,随人扰攘看交杯。”令人遗憾的是,近年来少数民族“非遗”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破坏和流失,内蒙古地区也不例外。
本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多种文化的星球》报告中曾经指出:“一种文化被另一种文化所摧毁,正如一个现存物种的消失一样,是令人不快的。”在您的调研中,当前在少数民族“非遗”保护方面还存在哪些主要问题?
郑福田:随着经济建设的推进和全球化的日益增强,随着科技手段和文化传媒的日新月异,少数民族“非遗”保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一是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与社会整体认同之间,尚存在一定障碍和偏差。在民族内部极为重要极具特色甚至关系到“根”的呵护和民族“基因”延续的项目,由于语言、习俗等差异,在社会上的认可程度与重视程度往往打折扣。“巴尔虎英雄史诗”在巴尔虎蒙古人中地位至为高崇,但由于是蒙古语说唱,未能成为国家级“非遗”项目;“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神话”在鄂温克族影响深远巨大,可却不能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十分遗憾。
二是内蒙古地域广阔,同一风俗在传承中略呈差异。特别是由于清王朝留给蒙古草原的制度遗产——盟旗制造成的有清以降蒙古族各个部落之间的分割和服饰、习俗之别,使今天的项目申报受影响。“祭火”本是蒙古人最古老极神圣的民俗,然因各地均有申报(“察哈尔祭火”“乌珠穆沁祭火”“鄂尔多斯祭火”),只好联合捆绑,终因各地形式内容不能完全齐一,未获国家级批准。于是,有的“祭火”成了自治区级项目,有的获得了盟市级项目,并因同为“祭火”为什么有等级之差引发质疑。可见,一项利于长远的文化政策的实施推广,须多层次、多视角关照,方可达成理想效果。
三是“非遗”保护专项人才匮乏,相当一部分“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老龄化严重,甚至出现“曲终人散”的结局。2005年10月,蒙古族长调歌王哈扎布以84岁高龄谢世。他生前能自由演唱的300多首长调名曲,现在百不存一,连一张完整的唱片都没有留下,不禁令人唏嘘。
四是相关政策法规(版权、专利权、外观设计权)制定实施严重滞后,形成知识产权保护“真空地带”,使仅谋求经济利益的开发有机可乘,造成一些项目民族、地域特点淡化,文化、历史价值式微。
本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少数民族“非遗”保护的重要性。我国也出台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在内的系列法律法规。在您看来,如何深入推进少数民族“非遗”保护?
郑福田:应以发展的眼光全链条审视,以改革的思维整体统筹,构建基础扎实、布局均衡、结构优化、内涵丰富的少数民族“非遗”保护新格局。
一是审议少数民族地区申报的项目时充分考虑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和心理期待,增加精通该民族文化的专家学者作评委,并组织专家学者在组织材料、申报填写等具体环节,给予申报方有效的指导帮助。
二是对待“捆绑式”申报的项目,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强调其反映的“整体民族文化”特点,容许项目内部因传承而形成的些微差别存在。比如,对待蒙古族“祭火”,就应重点考察它所带有的整个民族传承下来的凝聚情感方式以及它的文化价值。
三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保证“非遗”传承人在知识产权转变成经济价值时真正受益。由于信息不对称,内蒙古诸多“非遗”项目,被域外的公司、企业抢注商标。科尔沁蒙古族刺绣传人张春花作品被南方某纺织集团公司注册即是一例。建议当地政府提供相应的信息平台,公布传承项目和传承人姓名,还要帮助这些传承人尽早注册登记或打造品牌商标。政府应指派专人负责开通网上平台,帮助这些对多种途径传播的多元媒体并不谙熟的“非遗”项目传承人(特别是少数民族传承人)维权。要加快专项立法进程,提供法律保障,为少数民族“非遗”保护提供更多的依据和参考。美国1990年颁布的《印第安艺术和手工艺法》,就在全世界范围内有效地保护了印第安人的艺术与手工技艺。
四是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建立“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模式,全力保护和力挺自己国家的“文化黄金”,避免“非遗”自生自灭。这方面,法国1973年颁布“第二法令”,日本1950年颁布《文化财保护法》,意大利“反发展”的战略思路和直接给传承“非遗”项目者定期发放“艺术补助金”的做法,均可谓他山之石。
五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试行推广“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模式。这种“活水养鱼”的生态博物馆模式,是打破室内“博物馆”模式的新尝试,很适用于少数民族地区。如在一定的区域内,定期举办“歌会”“舞会”等游艺活动。内蒙古传统的“那达慕”大会就是一种很好的传播发展民族民间“非遗”项目的活动。内蒙古自治区的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游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鄂尔多斯市乌审旗蒙古族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都是地方政府依靠当地的生态、人文环境,在挖掘当地“非遗”项目经济价值的同时,又给予传承人经济保障的有益尝试。与此同时,还可打造特色旅游,如创建民俗村、“非遗园”、“非遗”交易中心,打造文化旅游节,等等。
六是在民族地区的大中专院校,设置“非遗”项目的课程,定向培养人才。采取鼓励措施,让少数民族青少年至少掌握一项本民族传统技艺。在科研立项、政府评奖、出版基金配套等方面,对以“非遗”为内容者实施政策性倾斜。
总之,权力杠杆和资金杠杆左右开弓,互动互补,想办的事情就一定能办到。